
《华尔街日报》推特截图
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,美国流媒体平台家庭大票房(HBO Max)决定响应一部分进步电影人的呼声,将1939的名片《乱世佳人》临时下线。
事实上,围绕着《乱世佳人》及其小说原作《飘》的争议由来已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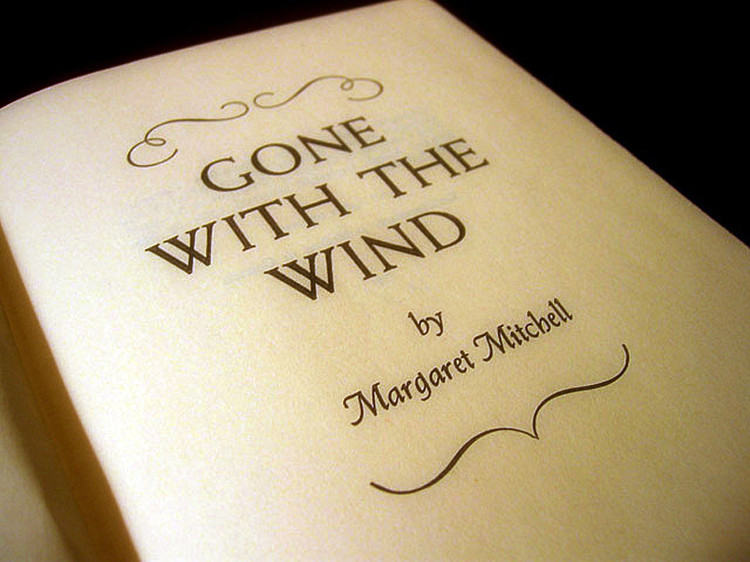
玛格丽特·米切尔(Margaret Mitchell,1900-1949)的小说《飘》出版于1936年,是美国当年和第二年的头号畅销小说,并得到了1937年的普利策奖。据以改编的电影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八项奥斯卡奖,并被视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影片之一。
1940年,傅东华的汉语译本《飘》在上海出版。
早在1981年,也就是傅译本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一年之后,《读书》杂志就曾组织专题,围绕着《飘》是不是反动小说,刊发了杨静远、肖穆和黄颂康的三篇文章。
“早就听说《飘》的观点是反动的。”杨静远开篇写道,“1975年,我开始读了一遍,觉得它的反动性果真名不虚传。”
她一眼就看出了《飘》是反动的,也许因为早在1958年,她就翻译过小册子《美国黑奴的起义》,1979年又译了《哈丽特·塔布曼》——杰出废奴战士和地下铁道史上最著名列车员的传记。
杨静远指出,对《飘》这本小说,美国人早就有认识,早就千方百计加以回避。1974年版的《美国百科全书》对它有如下评语:“把真正的南方人(指奴隶主)写成高尚的、不可屈服的;把北方佬(指反奴隶制北部人民)描绘成恶毒、腐朽的。奴隶制被看成一种仁慈的制度,而黑人则不是极端忠于他们的主人,就是野蛮兽性的东西。这本书是一曲对旧日南部的赞歌,它认为旧日南部是一种具有高度的美、秩序和风雅的文化。”(杨静远译文)

傅东华的汉语译本《飘》
但是,“对于《飘》这样一部在作者本国以及国外有较大的影响,至今读者不衰的作品,简单地用‘反动’二字加以否定是不妥当的。”肖穆辩护说,“在美国,它每年还要出版数十万册。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样一部作品。”
黄颂康则拿《飘》与另一部以美国内战和重建为背景的小说《欢乐的节日》(Jubilee)作比较。在后一本书中,黑人作家玛格丽特·沃克(Margaret Walker)根据她外祖母的口述,真实地描写了黑人的苦难史,《飘》却在不顾史实,一味地美化奴隶制。
在这一点上,郝思嘉常常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。例如,“那些北佬女人从前听说南方地主家都养着凶猛的猎犬,以备追逐逃走的黑奴之用,便都信以为真……他们又问到那种给农奴脸上烫字的烙铁,以及那种虐打农奴用的九个齿儿的铁蒺藜,其实南方地主并没有这些东西,都不过是北方人宣传的资料罢了。”
但历史文献已经一再证明了郝思嘉和她的作者在说谎。
《飘》也许有很多优点,但最大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缺陷,就在于它的虚伪。
至于“反动”二字,如果我们仅把它当作“进步”的反义词,那么《飘》当然是反动的。
郝思嘉不仅说谎,还非常虚伪。“从前那些做奴隶的一点儿也不苦恼,黑人在奴隶时代,比在现在这个自由时代还要舒服些的。你如果不信,你就向四周围看一看罢!”她说。
卫希礼也是虚伪的。他说:“从前的奴隶并不苦恼。而且,假使没有这次的战争,我也打算等父亲死后就把他们解放的。”
郝思嘉一向仇恨思想进步的北佬,敌视解放饿狼陀(亚特兰大)和曹氏屯(查尔斯顿)等邦联重镇的联邦军队,说他们一路烧杀、强奸、掳掠。不仅如此,小说还把三K党写成保护白妇白孺的人民武装。郝思嘉的第二个丈夫甘扶澜、大姑子韩媚兰、大姑夫卫希礼这些所谓的好白人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三K党。“当然,甘先生是在党里的,希礼也在党里的,我们所认识的一切男人都在党里的,”卫希礼的妹妹卫英弟很觉自豪地喊道。“他们都是男子汉,是不是?又都是白种人,都是南方人,是不是?他们去入党,你是应该觉得自豪的,不应该让他们藏藏躲躲,仿佛以为这事儿怪难为情似的。”
即使不以今天的标准来看,郝思嘉也是个典型的种族主义分子,在她眼里,黑人里除了少数几个忠仆,余下的非懒即恶。而不论忠奸,黑人总是愚蠢的——“你看,这些黑人多蠢啊!他们除了人家告诉他们的话,自己再也不会想一想的!怪不得北佬要解放他们了。”

《乱世佳人》剧照
郝思嘉对广大黑人群众充满了偏见和恐惧。她的偏见是种族主义者的典型偏见,她的恐惧是种族主义者的典型恐惧。她常常“想起那从黄昏中向她窥视的奸恶的黑脸”,也常常“想起那只在她胸口乱摸的黑手”。“她在烂泥中滑得歪歪斜斜地走着,还不时地停下来喘气儿,拔鞋跟,匆匆在那些个黑人身旁走过,他们都没有礼貌地咧着嘴笑她,还互相哈哈大笑呢。这些黑皮猴好大胆子,竟敢来笑她!竟敢咧着嘴笑塔拉庄园的斯佳丽·奥哈拉!她真想叫人用鞭子把他们一个个都抽得皮开肉绽、鲜血直流。北佬真不是东西,竟然把这些人给解放了,让他们肆无忌惮地来嘲笑白种人。”(此处引吴信强译文,因为傅东华的译本里把这一段跳过去了)
有一种可耻的流行论调,说既然黑人认为美国不好,那他们为什么不回非洲去呢?塔布曼对此早有回应:“白人把黑人弄到这儿来替他们干重活,现在白人又想把黑人连根拔起送回非洲去。但是他们办不到。我们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,他们没法把我们拔掉。”杨静远说,“这些掷地有声的话,对于那些至今还想把黑人撵出美国来解决种族问题的人,是有力的批驳。”
对美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,也可以这样质问那些要把黑人赶出美国的声音:既然白人认为美国不好,那他们为什么不回欧洲去呢?白人实在是比黑人更有理由回到他们原来的大陆上去的。科尔森·怀特黑德在小说《地下铁道》里,曾借着废奴分子和演说家伊莱贾·蓝德之口说:“白种人相信,发自内心地相信,夺取这块大陆是他们的权利。屠杀印第安人。发动战争。奴役他们的兄弟。统统都是他们的权利。如果天下还有一丁点儿的公理,这个国家就不应该存在,因为它建国的基础是谋杀,盗窃,残忍的恶行。”
《飘》充满了种族主义的偏见,在美国人民日益要求进步的今天,它的不合时宜甚至反动的特性就显得更为突出。因此,像家庭大票房那样,在不触及原作本身的前提下,为它补充一些说明,指出创作者对奴隶制的美化背离了历史真相,借以对今天的观众作一些提醒,难道不是一种善意的和必要的举动吗?